伤痕文学(painnovel)
落果
《落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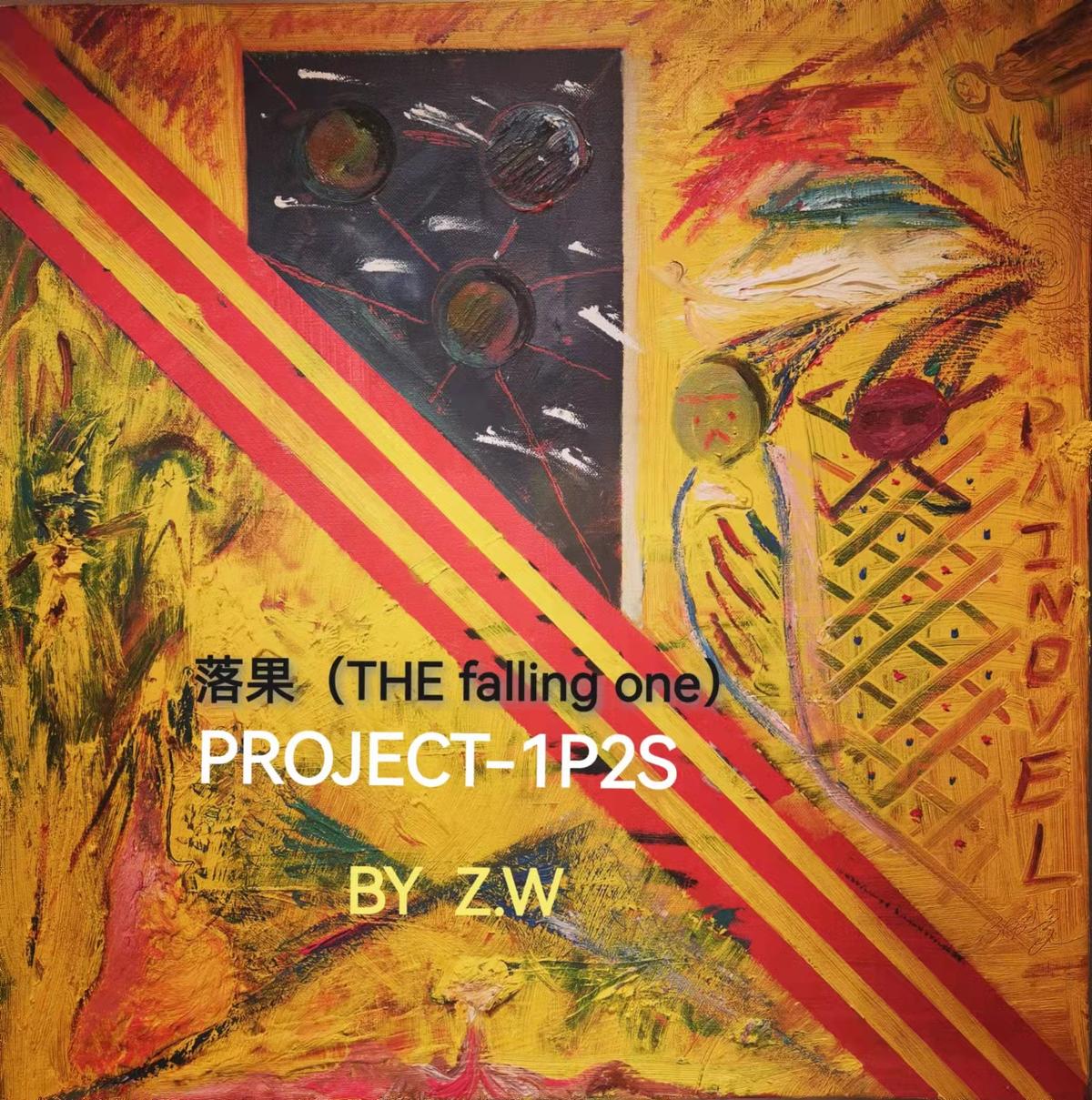
1. 卖相
洛果回宁波后一直租住在我名下的一套市郊公寓。关于租金的事情,我俩因为嫌麻烦至今没签任何书面合同。我们保留着应家村的人靠嘴巴来约定事情的传统习惯,说好28号是付房租的日子。这样的规则在深受“猜疑链”危害的城市里因水土不服而显得有些好笑。以至于同事们觉得我现在“出息”了,在郊区养起了“小玫瑰”。我最初喜欢解释一下,但效果并不理想。
:“她每个月付我2200房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呀,男人嘛,懂。”
中年的男人似乎掌握着世界的发言权,他们觉得你不懂的事情,你万不可能明白,假使明白,必然只明白到了皮毛;他们觉得你该懂的事情,你必然是懂的,假使懵懵懂懂,必然只是懂装不懂。这是“小玫瑰”事件给我带来的启发。
我毕竟也是要结婚的人,不能让谣言再这么猖獗,于是最近还是决定找上洛洛,随便签个像样的“租房合同”。
我告诉她,别人说你是“小玫瑰”。
她告诉我:“哦。”
:“部分中年男人因为文化有限,喜好把女人比作玫瑰,但并不是说这是个好词哎。”
他说:“嗯嗯。”咽了咽口水问我----我觉得她像什么?
我想了想,想了又想……
2.定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样的果子,个头不算太小,当然也说不上大,看上去不会太甜,但总归是能吃的样子。像从地里长出来似的自带一层轻薄的浮土——不太干净的样子。外公告诉我这样的果子很差,很差到采购员会仔细检查鲜果里有没有混进它们的地步;外婆告诉我这样的果子很多,多到我们一家人都吃不光的地步;我妈告诉我这样的果子很脏,脏到如果真吃进去就会拉肚子的地步。 长辈好像都不喜欢那些果子,如果一味听信他们的教诲,任凭谁都会觉得它们只是存在就已经犯下了错。可做什么样的事情是犯错,什么样又是正确呢?那是我很后来才会去想的事。是洛果在一个春天告诉我,这些掉下来的果子糖分是最足的
“别看他们丑兮兮的,它们摔下来之前,比那些在树上的好看多了”。洛洛说着递给我一个沾饱了井水的果子
:“尝尝”。
我头回见到这种果子干净的样子,表皮紧致细嫩,一块乌黑的淤青格外显眼。洛洛让我用牙齿把发黑的地方给咬下来。
“只是一点点不好的地方,没有了就可好吃啦”。
我照做后把其余橘红色的果肉一口吞下——比起树上那些还没熟透,坚实精致的果子,刚刚的果子确实甜的很不一样。
“对吧?”。
“对啊,对啊”。
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嚼着洛洛洗干净的果子,在想大人为什么要骗人;那时候我大概没什么烦恼的样子,嚼着洛洛洗干净的果子,在想洛洛为什么没被骗。 可能她比我聪明吧?
3.育种
洛洛比我大两岁,她的家在应家村东边的一处矮房,和外婆家隔着一条浅浅的河,河西是村里最大的市集菜场,东边则全是大块的泥泞田野。洛洛最早和我们家一样住在西边,是因为长辈赌博之类的事,搬到了破败的东村。 关于洛洛爸爸输光菜场门口连排商铺的八卦,村里大人们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他在网上赛马,用真钱以1:1的比例兑换虚拟币下注,赢了想乘胜追击,输了又心有不甘,每当余额不够了算法就会在主屏上显示周到的贷款抵押流程。如此反复之下,自然是有亏无盈。妈妈说那个男人也并非是真正的赌徒,在最后的确有过止损的想法,只是那个网站充值起来各种满十万送五万,提现时却扣扣搜搜的限制起了每日额度。
:“开始是骗钱,之后变抢钱了啊”。
出于好奇我追问道:“一天最多能提多少啊?”
“一万吧?”想了想妈妈又纠正道,“不是一天,是一周。”
我得知后脑海浮现一个诡异的画面——男人额头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强忍住恶心和愤怒,犹犹豫豫的点击鼠标左键,一旁的手机霎时传来比肖邦更美妙的旋律。伴随屏幕发烫的字幕“您尾号7016的储蓄卡1月5日23时54分收入人民币10000元,活期余额10003.06元。客户附言:积分提现。[应家农业合作银行]”
男人回想起学生时代某一次成功的考试作弊,此时此刻正如彼时彼刻似的,分享着极为相似的快感与寒意——用极端的手段去偿还过往的余罪,霎时像是度过了难关,可难关后却是无尽的难关。 这样的日子还会有很多吗,从年轻到如今?从富翁到如今?
据说在男人开始连续“割肉”的第四周,平台就以“涉及安全违规”为由,封禁了他的账号,当然了,也封禁了他靠账户里残余的三十来万积分开个烟杂店的念头。
出于这些原因,这个没有了念头的男人在大概非典前后的一天离开了正和我在地上捡水果吃的洛洛,留下四万块钱——鳞次栉比,罗列在血红色的雕花檀木上。比红色更红的红色像是浩瀚的楼盘广告般留给过往行人繁荣的红色想象。
4.生长
西村旧宅卖掉前一个月,热心的外公参与了洛洛家手忙脚乱的善后工作----银行存钱;向东搬家;家当出售……我们以此为契机才在果园说上了话,吃到了又脏又甜的果子。我对洛洛的大胆表示认可,她很老成的模样告诉我说:“大人说的不一定对。”
我小心翼翼的回应说:“我偶尔也这么觉得。”
我今天写到这里很喜欢当时的情景,两个被大家认为交不到朋友的坏小孩成为了彼此的朋友——这里头有一些对人性的信任,有一些对时代的反抗。 说到底果子甜不甜到底是由大人说了算还小孩说了算呢?其实都有失偏颇,该由吃的人说了算。摸着这样的观点继续深究下去,果子好不好是靠甜度决定还是靠品相决定呢?其实也不好说,毕竟谁规定的果子生下来就活该被吃呢?
谁又规定了谁是正确的人呢?
5.同类
我们几乎在03年之后的每一个暑假都会见面,于是村口常常可以看到一团黑色的煤球被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子拉着手从村子的西边往东走,个别不怀好意的村民们对此有一句押韵但无理的评价“城里人的黑胖儿子和赌鬼家的太妹女儿。”我不知道洛洛对此怎么想,但我十分在意,在意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叫“青梅竹马”,我们怎么就成了“臭味相投”呢? 关于我们俩不被大人待见这件事,我至今觉得错不在我们而在于刻板的标签和轻浮的流言。
:“站在被评价的角度,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件当代艺术。”我这么和洛洛说。
:“怎么讲呢?”。
:“好坏全凭一张嘴。” 洛洛听完泛起一阵苦涩的笑意。一时语塞,沉默结束后竟提起了奥运会那年的事----我以为她不愿意再去提的事。
:“我很在意!不是因为委屈或是生气的原因而在意,而是因为再也没见到过你而在意。”
洛洛讲这话时牙齿因气愤而微微发颤。2月的空气竟会闷热,像是回到了应家村的暑假。那个洛洛为了我不被起诉,对外承认自己和一个黄头发的高中生是情侣关系的暑假……我想村里人大多数知道那个高中生只是个猥琐的“内衣贼”。但热衷故事的时代,比起小偷小摸的色狼行为,大家更喜欢听到不良少女趁暑假和高年级的哥哥在家里“开房”。
“我哪怕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纠缠在对和错之间,耗费几乎是要溢出来的善良,换来大把的麻烦和嘲讽。”
“像08年那样的事,你后来还做过很多嘛?”洛洛问我的语气很淡。
“呃……有的,有一些。”我回答的语气很轻。
:“我也没那么生气啦……”
奥运会之后的12年;“开房事件”之后的12年,我们再也没见过。如果不是因为应家村的拆迁,我也不会凭空得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洛洛也就不会阴差阳错成为我的租客,这样一来,上面的谈话,谅解也无法发生。假如真是这样,我可能至今都会对那个伸张正义的下午懊悔不已。
6.骤雨
奥运会那年的时间非常特别----特别在我小学毕业的同时洛洛即将备战高考。好像一夜之间洛洛就变成了广义上的大人;而我却只是个提前放了暑假的小学生----虽然我们照旧相差两岁。
大人都是有烦恼的,那年的暑假开始前,洛洛告诉我以后不能再一起去田里烤火了,她得做大概两斤的暑假作业。我当时一方面懂事的表示理解,一方面出于无聊,会在下午爬上高高的水塔用望远镜看看洛洛是不是真在好好学习。如果她计划和我一样偷懒的话,我就计划用激光笔照照她。
这样无聊的恶作剧并没有等来洛洛的偷懒,反而让我观察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家住西村的胡淼常常一个人出现在洛洛家的晾衣架附近。待的时间倒不久,只是探头探脑的做派,实在不像正常的路过那么简单。至此我便把观察的重心从洛洛转向了胡淼----直觉告诉我他在做一些很猥琐的事情。
当时我试探性的问洛洛家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得到的回复让我十分震撼。
她说:“内衣经常不见。”
得知这个消息的我,对这件事大概有了些判断,喷涌而出的个人英雄主义让我仓促的决定,在洛洛不知情的情况下,保护好我的好朋友。这也是一切错误的开始。
如果你们以后也想做一些正义的事情,劳请和我一样,先考虑后果,再考虑对错。
7.暴风
“这确定是威力最大的了?” “弹丸虽然是塑料的,但枪是实打实的铁皮”这是西村文具店的老板在跟我打包票。我去那的目的和以往比起来有些不单纯——以往打枪是为了代入虚幻的个人英雄主义,那样的前提下,气枪重要的是声音是否响亮;这次为了真能把人打疼,才需要考虑威力,至于声音反而是越小越好了。 发育不良的我揣着塞饱了弹的手枪,眼前是比自己高出两个头的高中生。出于害怕,我的声音虽大,却止不住颤抖
:“你拿洛洛的内衣干什么!”
接受质问的人并未表现出接受质问者应有的紧张,这是我之后情绪失控的重要诱因。高中生熟练的把烟头丟向附近的田埂,以那种自以为幽默的语气反问道
:“你?这么个小不点,也有这种爱好?”
:“我生气了!”
枪膛瑟瑟发抖,我也瑟瑟发抖,空气没有声响,喘息声倒像八月的台风,吵闹个不停,为了打破当下无人理睬的尴尬局面,我示意高中生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那个哥哥意外的非常配合
:“你有这种爱好?”
又是一句轻飘飘的疑问掷出。 问句轻飘飘,打到左眼的那发子弹却不含一丝戏谑。第一声“啊”由愤怒的我传出,第二声“啊”则来自痛苦的他,彼此交织配合后响彻了整个村子,我在之后了解到这样的技巧叫做和声,不禁感慨到音乐真是个需要情绪才能去从事的行业。
说回那一天,从子弹出镗到警察来外婆家问话其实是在一个钟头内发生的事情,但于我却像一个世纪般的漫长。五年前在家等债主电话的洛洛爸爸会不会和在家等警察上门的我分享着同一份忐忑呢?
----哎呀,原来很多事情不是假装不知道就不存在了呀。
8.培养室
村支队的警官叔叔对他的同事夸我牛逼。“双亲健在,有车有房,适龄上学,十二岁来写笔录的小学生真你妈头一回见,你妈的真是牛逼!”我听到了也觉得自己牛逼,只是又牛逼又害怕极了。现在我能记起很多的事情,却唯独记不起那天类似于审讯的问话——
一场雨细密的覆盖了应家村的街道,视线严重受阻,我的左边是泣不成声的妈妈,眼前是一副手铐,又也许不是——我的手太小了,乡下的派出所可能不会有这个尺码。警察先盘问的是妈妈,可眼前这个本分的女人因为抗拒现实而出现了轻微的精神错乱,警察问她名字都要掏个身份证照着念。反而是我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表现出了类似成年人的冷静,不紧不慢的撒了人生中第一个谎——“是那个哥哥先动手,我刚好带了这把玩具枪。”
雨天里的我一边将虚假的回忆娓娓道来,一边将因害怕谎言被拆穿而流下的泪水,伪装成因害怕恐怖的回忆而流下来的样子——以次充好!
其实我哪怕不写那些歌,那些画。依照那天的表现稍加训练,当个演员也是远在及格线之上……听说几公里外的高中生那时正因晶状体的轻微变形而疼痛不已,卫生院的医生对此好像缺乏一些经验,建议往城里送。她的妈妈歇斯底里的嚷叫着为什么那么大个医院,除了给伤口消毒,啥也不会。护士长闻声赶来,打鸟似的让几个年轻的护士散开,耐心的开始科普有关排班制度,执照审批,行医流程,重点难点之类的东西。
房间里的老医生尴尬的用较为专业的试剂一遍又一遍的清洗着高中生不时渗血的创口。我告诉我的房客洛洛,那画面应该很像上个月给我剪头发的一个理发师。
“和义大道剪一次头要四百。”
“啊?!”洛洛对此只回应了一个字。
“就,就很像那天的医生啊,明明弄不出什么花样,但为了证明自己是有点用的,一遍遍的重复着没有坏处,也没有好处的动作。”
“那要重复到什么时候哦。”
“重复到我变成一个帅哥。”
“啊?!”
那天的我没有变成一个帅哥,那天的高中生也没有等到城里来的医生。两者都较为不幸,但比起不帅这件事,提前戴上老花镜的高中生的确更令人惋惜。
:“胡淼到现在都都戴着特制的眼镜,左边是老花,右边是近视,滑稽的很。”洛洛说到这里露出了今晚的第一次笑容。啤酒杯也连带着被身体的颤动牵引发出咯咯的曲调“豪豪,这些医生真是帮大忙了。”
让她笑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来的容易啦……
我倒不认可洛洛的观点,如果那些医生愿意承担责任,积极的去救治,去联络。而不是一遍遍的做些消毒,清洗的正确又无用的工作。也许胡淼的眼睛不会落下病根,那事情就不至于糟糕的要签署谅解协议的地步,我也不至于至今对洛洛有所亏欠。如此看来,事情又得说回所谓“正确的人”,如果单是擦药自然不会犯错,但诺大的村卫生院体制内,总该有个喊话的人吧,叫救护车也好,取出子弹也好,报警报案也好……人人生怕犯错,人人生怕担责,人人想做正确的人因而人人都不正确的离谱……大家以后果然都得这样才能生活嘛?躲藏在森严的体制之下,吸吮时代进步的红利,自觉的只要不犯错便等同于在进步,只要在忙碌便等同于在做事。多久呢?久到大厦倾溃?久到人人自危?
我告诉洛洛“那些医生没有帮大忙。”
9.欲坠
谅解书严格上的说法叫《刑事谅解协议》主要用于被告方不被逮捕,不被起诉,争取缓刑。也就是所谓的“三不一缓”。这是我在小学就了解到的法律知识,不知道现在是否依然如此。 胡淼的左眼当时失明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他腿脚不便的外婆每天都会举一块潮湿的木板,出现在我即将入学的初中门口。好在那时候暑假刚刚开始,只有过往的行人和偶尔来开会的老师会看到这位可怜的老人。因为不识字,木板上的内容临摹的歪歪扭扭,写着
“还我孩子眼睛”。
劣质红漆在七月高温的催化下向整条小巷弥漫,终于吸引到了校长的注意。他在一天早上,把老太太请到了办公室询问具体情况。 听说老太太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噗通一声跪下,脆生的骨骼和斑斓的大理石碰撞出奇妙的声响。吓得老校长赶忙把关上的大门又给打开后,转头也单膝迅捷地跪在老太太的面前。他们最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彼此信息的交换。校长问老太太有什么诉求,她几乎没有思考就回复道:“让他退学” “让他退学” “让他退学”......
老太太试图用积攒下来的悲痛赋予贫瘠文字更深刻的表现力。无论校长回应缜密的逻辑或是温润的鸡汤,她都只重复着四个字。最后是支队的民警连哄带骗的把老太太带上了警车才平息了那场闹剧——他们先让老太太去车里休息,养足了精神再去盘问校长,只是一上车就笔直的往东村的家里开去。发觉上当的老太太一路哭嚎,这次说的是
:“谅解协议不是我签的。”
10.失重
谅解协议当然不是她签的,是胡淼乘外婆睡着的时候按上去的。做为交换,洛洛和胡淼在东村的卧室洗出来一张举止亲密的合照。这样的好处是,胡淼从一个猥琐的内衣贼变成了潇洒的“不良少年” ,顺带让我变成了爱而不得的小学生追求者。
胡淼这样做的坏处是,后续的赔偿和维权会因为这样一纸协议和他本人的“大度”而困难重重。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相比于钱,小孩子会觉得面子更重要些。 洛洛背着我去做的这些;就像我背着洛洛去做了那些。但如今看来洛洛要是没了我,顶多会少几条内裤;我要是没了洛洛,也许会背上厚厚的案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蛀虫。 :“洛洛啊,我从小自觉正义,不让人省心。” :“你把这个月房租免了,就当我积德了。” :“你要愿意在宁波安安分分的呆住,别折腾,别乱跑,这房子你交个水电就好。” 洛洛听完熟稔的点起一根烟,边点头支持我的好意,边借着微醺自言自语道:“本来我也有的…我也有的……我也……我也有的。”
11.对照组
本来她也有的东西是指房子,08年的事情传的满城风雨。尝到甜头的“完美受害者胡淼”当时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和身边的一众狐朋狗友讲述自己从网上学来的关于爱情的体验。有了洛洛的伪证和家里“不小心”被发现的二手女士内裤,男孩子们对胡淼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自此村里的洛洛便像园里的夏娃一般,和“性”有了一种神秘,龌龊的关联。在大环境的凝视下,村里人仿佛比洛洛自己更了解她的身体。 :“在白天我以为自己可以不在意,但那些闲话到了晚上就会迅速占领意识。让我活的越来越像闲话里的自己。”这是洛洛今晚对08年的评价。 属于她的少女时代好像自那以后便一去不返,接踵而来的是嘲笑,搬迁,学习,考研,北漂,海漂,蜗居……
:“你是因为这个迁的户口?”
:“是啊,10年搬走,11年拆迁,你说豪豪,人要那张脸有什么用?我就是为了这张脸,快三十了还在租房子住,我……”
她还准备说些什么,但被几乎要烧到食指的女士香烟打断。我凭借小时候的默契,把她想说的继续了下去:“你知道我在为你出头,所以你也想为我出头,但应家村就是那个样子啊,容不下坏人,但越是坏人才能生活的越好。
:"对了,孔家村会拆吗?你妈妈在那边不是也有地的。”
:“不会的,那里离庄桥机场太近。”
:“哦,这样啊,太近了,不能盖高楼的,不能的。”
12.争议
前阵子我在奶奶家睡觉的时候常常能听到训练飞行的轰鸣声,各地也总在传闻要开战的消息。但说这些话的人大多身居高位无所事事或足不出户无所事事。
其实我和洛洛这样每日需努力工作的普通人,是无暇关心所谓的“开战”,“收复”的。我们只是关心好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以后便精疲力尽了。
但打开新闻或是网站之后,黑压压的舆论和评论便向每个不曾表态的群众施展压力。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觉得台湾省的人如何?你知道台北市,桃源县,龟寿路有个大学生偷了健身房的跳绳吗?知道了后是否觉得台湾人素质很差?什么?不觉得?那你就是觉得台湾那边的素质比大陆好咯?那你支持统一吗?既然支持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说台湾人素质差?
如此种种之后,质问的声音精疲力竭,被质问者精疲力竭。精疲力竭好像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他们要追求的结果,好像一旦精疲力竭后,什么结果都是“努力后的结果了”。
想到由庄桥机场影响拆迁带来的种种困惑,我向她埋怨:“大人们把世界搞的乱七八糟,把自己搞的大汗淋漓,把我们搞的尴尬难堪,末了还不忘擦一把豆大的汗珠告诉我们“还好我们一通瞎搞,不然这世界会更乱七八糟嘞。”
:“真是够乱的,那你后来还见过那个偷我内裤的变态嘛?”
:“呃,见过的,他家也拆了,买了辆黑色的宝马车。工作就是开着那车去江北那片认识外地来打工的女孩子。”
“死性不改。”洛洛说完以后见我接不上话,便又自言自语着“我要是在上海的时候就能想到攒钱付首付就好了”之后便是一个月花五千,能存两万……一年就是二十四万,两年四十八万,亲戚那边可以借到……洛洛的算数到了尽头,眼睛里的光也淡了下来,垂头丧气的把脸搁在了自己的左手,自己和自己置气的说道:“全给我用来买包了。”
:“要……要培养正确的消费习惯呀。” 我没告诉洛洛,其实我也有一辆黑色的宝马车。
13.落果
好像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人来说,拥有什么并不取决于能力,而取决于需求——小时候需要足球,长大了需要电脑,工作了需要汽车,结婚了需要房子之类的……而对于另一群人呢,尚且不要谈及拥有外物,单是让自己存在也需要全力以赴才可以。
我来签合同那天,俄罗斯正和乌克兰闹的凶猛。车外下了绵密的雨,我的驾驶习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用雨刷——烦人的电器声。于是任由一只褐色的细腿蜘蛛被风送到车窗上。我想看他能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停留多久。
能看出他是蜘蛛里比较机灵的那种,精准的规划路线,一边规避银针似的细雨;一边试图往地势平坦的车顶爬去。我看着它聪明努力的样子,觉得它总该能如愿的——到高处,等天晴,等车停,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也许是庄桥附近的一处残垣,有自己的网,在夏天抓一些喜欢的虫子,在冬天睡着或死去……只是车子兀自的发出一声嗡鸣,雨滴化成了一滩水,蜘蛛化作了一滩落果——褐色的,平面的,刮不掉的。
哦,我那时候想起来了,宝马车的雨刷是自动开的。
